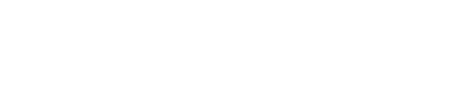老白杨——鸡声
专业号:鄱湖人家 2019/9/25 8:14:54
山村,用鸡声,喂养了,我的童年。
太阳,还未爬上东山偷窥,村头,大伯家藏匿于竹林中的鸡声,就醒了。接着,山村也就醒了。跟着醒来的,还有,山野拉着犁的水牛,注水入田的渠声,禾苗的拔节,巡田人踏碎蛙鸣的小唱。
太阳,终究敢爬出东山了。烟深处,鸡声响成了一片,闯出每家每户的篱笆,朝山野奔来。
我的童年,最爱听的,还是祖母养的,那只母鸡下蛋后的叫声。当母鸡,从竹篱边的窝里钻了出来,就骄傲地,立于院中叫得正欢。此时,我就会快速地钻进鸡窝,扒出一个又大又亮的鸡蛋,叫着,跑着,交给祖母。我知道,久已断奶的铅笔、作业,又有了着落。
童年,我听着鸡声长大,鸡声,喂壮了我的梦想。
人到中年,我常常漂泊。追寻生活的脚步,长期在城镇的街头流浪,多想听听曾经熟悉的鸡声。
有时回到故乡,祖母走了,母亲老了,当年的鸡窝,蜷缩于竹篱边。长满荒草的小院,圈养不出一句鸡声。
春风吹醒的绿草,从田野爬进了村口,再翻过篱笆,向涌入城市人家的门前场地上蔓延,若大的村庄,靠几位翁妪守着。
当太阳走过村头的竹梢,不知何处,跳出了几句瘦弱的鸡声,叫醒了几缕炊烟,从瓦屋的瓦缝中钻出。咳嗽般的鸡声,跟着病恹恹的炊烟,翻过竹林,向沉寂的田野逃去。
中年,听故乡的鸡声,就像一个久离母亲的游子,归家时听到母亲,呼唤自己的乳名,既亲切甜蜜而又涌起一番苦味。
如今,我是一只,背着夕阳,在暮色中飞翔的鸟,久已飞离了山谷,习惯在城市的园林中筑巢。
很久很久未听到故乡的鸡声了。每当,晨光在高楼的上空苏醒,夕阳在长街的尽头留连,我总是习惯地倾听远方,想听听熟悉的鸡声。鸡声,仿佛失踪似的,躲着我。此时,我只好吟唱起前人的诗句来:
鸡鸣桑树颠
雨里鸡鸣一两家
鸡声茅店月……
我就用这些诗句,勾起我对故乡鸡声的想象。
我儿子与孙子,都是在城里生,在城里长,此时,听着我念着有关鸡声的诗句,他们都会用奇怪的眼睛盯着我,连这些诗句,都不愿念了。
故乡的鸡声,让我听着流泪,可在儿子孙子的心里,已经失传了吧?
1.依据《服务条款》,本网页发布的原创作品,版权归发布者(即注册用户)所有;本网页发布的转载作品,由发布者按照互联网精神进行分享,遵守相关法律法规,无商业获利行为,无版权纠纷。
2.本网页是第三方信息存储空间,阿酷公司是网络服务提供者,服务对象为注册用户。该项服务免费,阿酷公司不向注册用户收取任何费用。
名称:阿酷(北京)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联系人:李女士,QQ468780427
网络地址:www.arkoo.com
3.本网页参与各方的所有行为,完全遵守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》。如有侵权行为,请权利人通知阿酷公司,阿酷公司将根据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删除侵权作品。
 m.quanpro.cn
m.quanpro.cn